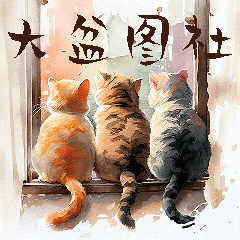我这一辈子,最大的错误就是信了“心想事成”这句鬼话。这导致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,只要一闭眼,就觉得自己在撞墙。
那时候我年轻,虽然看起来蔫头耷脑,但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是个搞技术的料。我不信鬼神,只信公式。我觉得神仙也就是掌握了某种高级物理规律的人类,比如牛顿或者爱因斯坦,只不过他们没把公式写在黑板上,而是藏在了《道德经》里。
所以我去了崂山。不是为了长生不老,是为了穿墙。
收留我的老道长,留着山羊胡子,眼神像看傻逼一样看着我。但我看他的眼神,像看一个掌握专利技术的奸商。
他让我砍柴。三个月。
我一边砍,一边在心里算账:这堆柴火燃烧的热值,如果转化成电能,够不够驱动一个粒子对撞机?如果不够,那我凭什么要用这些无意义的体力劳动,去换那个据说能改变空间结构的“穿墙术”?
我去找他谈判。
“师父,咱们搞搞清楚。我是来学技术的,不是来给您当林业工人的。这三个月的劳务费,您是不是得折算成学费?”
老道长盘着腿,吐出一口烟圈:“孺子不可教也。心不诚,术不灵。”
我心想:这分明是典型的“技术壁垒”话术。他就是不想免费开源。
终于,他看我快要把崂山的树砍光了,才勉为其难地教了我口诀。
“穿墙术,关键在于‘无’。你得把自己看作一阵风,一缕烟。”
我试图用量子力学去解释它:是不是通过改变自身的波函数,让自己产生“隧穿效应”,从而越过势垒(也就是墙)?
但我还是没忍住问:“师父,墙是由硅酸盐和钙离子构成的,我的身体是由碳水化合物构成的。如果我要穿过去,是不是意味着分子间的电磁力要暂时失效?这需要多大的能量?我吃那点馒头够用吗?”
老道长恼了,拿拂尘抽了我一下:“闭嘴!让你穿你就穿,哪那么多废话!”
我明白了,在这个领域,逻辑是行不通的,你得靠信仰。这就像相信领导画的大饼是真的能吃的那种信仰。
下山那天,我信心满满。我觉得我已经掌握了宇宙的真理——只要我不尴尬,尴尬的就是别人,或者那堵墙。
我来到县城第一中学的围墙边。墙那边有我心爱的姑娘,还有食堂的红烧肉。墙这边,只有贫瘠的现实和几个正在打牌的保安。
我深吸一口气,默念口诀,心里想着:“我是风,我是烟,我是虚无……”
然后我像一颗出膛的炮弹,冲了过去。
砰!
那一瞬间,我听到了我鼻梁骨碎裂的声音,清脆得像 snapping a carrot(咔嚓一声脆响)。紧接着是剧痛,那种痛让我确信,物质是第一性的,墙是客观存在的,而我是傻逼。
我捂着脸躺在地上,鼻血流得像开了染坊。
保安围了上来,其中一个还踢了我一脚:“偷窥狂?还是想越狱?这墙是刚用水泥砌的,硬着呢!”
我躺在地上,看着灰蒙蒙的天空,突然悟了。
老道长没骗我,“心诚”是真的。
因为只有脑子有病的人,才会真的相信自己能穿过去。
而我,虽然脑子有病,但我的身体非常诚实,它忠实地遵守了牛顿力学。
后来我又回崂山找老道长。
“师父,您那法术是假的。墙太硬了。”
老道长正在喝茶,眼皮都没抬:“不是墙太硬,是你太硬。你心里有鬼,所以穿不过去。”
我反驳道:“师父,这叫客观规律。您那是唯心主义,迟早要被唯物主义砸烂脚后跟的。”
老道长把我赶下了山,说我“根器太差”。
其实我知道,他那是心虚。他也不敢去穿县委大院的围墙,他只敢在深山老林里穿穿那种年久失修的土墙。
现在我的额头留下了一个大包,像长了第三只眼。但这只眼看不见未来,只能看见荒谬。
每当有人跟我讲大道理,或者让我相信某种奇迹时,我额头上的包就会隐隐作痛。它在提醒我:别信那些穿墙的鬼话,路只有一条,那就是绕过去,或者翻过去。硬撞,只会把鼻子撞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