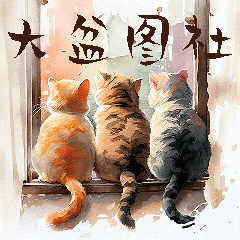糯米是头夜便淘好的,浸在井水里,一粒粒胀得晶莹。清早捞起来,搁在木甑里,灶膛里烧着松柴,火舌头舐着锅底,水汽便袅袅地蒸腾上来,将灶间的梁木都熏得润润的。母亲将那蒸熟的糯米倾在竹匾上,摊开,山间的风便轻轻地来,将那腾腾的热气与米香,一丝丝地收拢了去。待到手探进去,只觉温温的,便可用手细细地搓,将那黏作一团的米粒都搓散了,像搓散一捧玉色的沙。这时节,才将赭石色的酒曲,匀匀地拌进去。那曲子是祖传的,藏着山里草木的魂魄。末了,倾入粗陶的缸,舀几瓢后山引来的泉水,那水是活的,清冽冽的,带着岩石与苔藓的清气。缸口蒙上厚布,用麻绳扎实了,便只等光阴来点化了。
这般的酒,酿上三个月,便堪作料酒了。煮鱼炖肉时,浇上一勺,那股子醇厚的香,便将腥气都化作了馋人的鲜。酒糟也有酒糟的造化,拿来腌菜,菜便有了隽永的底味;煮泥鳅,那泥鳅的肉便格外滑嫩;若是焐一块五花肉,油脂沁到糟里,肉烂糟香,是能让人多吃一碗饭的。然而这终归是“用”的物事,算不得席上的珍品。
珍品是那些在屋角阴凉处,默默守了三五年的老酒。缸身的陶釉,被岁月磨得温润了,里面却是一场静默而剧烈的嬗变。酒色由清转浊,又由浊沉淀出一种温润的澄黄,像将秋日的阳光也酿了进去。这样的酒,是只在要紧的席面上才肯请出来的。红事白事,人情冷暖,似乎都要靠它来作个见证。家境拮据的人家,酒里掺了水,喝起来便只是淡淡的,图个热闹罢了,席散时,人也多是清醒的。可若遇着那珍藏的老酒,情形便不同了。
尤其是冬日,将那陈年的酒从缸底小心地舀出来,倾在锡壶里。切几片当归,几缕老姜,再投一块黄冰糖,在炭火上慢慢地煨。酒香便混着药香、糖香,暖暖地弥漫开来,驱散了屋里所有的寒意。煮开了,便挪到火盆边,让它在灰烬的余温里,保持着那般恰到好处的暖。斟一杯,那酒液在粗瓷碗里,漾着琥珀似的光。入口是甜的,是糯米的魂魄被岁月磨成的圆润的甜;继而一丝当归的苦意与姜的辛,隐隐地透上来,却不恼人,只将那甜衬得更有深意。女孩子们也爱这温润的滋味,捧着小碗,能喝上小半碗,脸上飞起两朵红云,眼波便也像那酒一般,温温地漾着。
可这温润的甜香里,却藏着些凛冽的东西。村里人唤作“被酒药倒了”。那不是寻常的醉,寻常的醉是渐渐袭来的困乏与欢喜。这“药倒”,却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,从温香的酒液里陡然伸出来,在你的后脑轻轻一拂,人便忽然地、毫无预兆地断了音讯,沉到漆黑无梦的渊底去了。待到第二日挣扎着醒来,脑袋里却像经历了一场无声的鏖战,只剩下一片翻江倒海的钝痛与空茫。老人们说,这是酒里的“酒药”太凶,是那陈年的魂魄里,有些不安分的、过了火的东西。
后来,也不知是谁从山外带来了新的见识,说那叫“杂醇”,是自家酒曲与山水,在漫长的守候里,偶然生出的邪祟。它不像寻常的酒力,让你在醺然中慢慢倾倒,它是在你最不设防的温甜里,骤然给你一击的。这见识一传开,大家再看那些澄黄的老酒,眼神里便多了层复杂的敬意。那敬意是真的,畏惧也是真的。再香甜的引诱,也抵不过对那骤然“断片”与次日“脑浆翻腾”的恐惧。温暖的、需要耐心与仪式去对待的黄酒,便这样,在山民的席面上,渐渐地隐去了。
如今回去,席间多是金黄的啤酒了。即便是三九寒天,也要从冰柜里取了来,玻璃瓶上凝着一层冷露,握在手里,是扎人的凉。仰头灌下去,一股清冽的、带着气泡的苦味直冲下来,爽利倒是爽利的,却再没有那种从喉咙一直暖到心底,继而将四肢百骸都浸润了的温存了。那冬日里煨着当归、姜片与冰糖的锡壶,那在火盆边闪着温润光泽的琥珀色酒液,那在甜香中不知不觉降临的、温柔的陷阱……都成了真真切切的传说,沉在记忆的缸底,偶一搅动,泛起的气味,一半是勾人的暖,一半是凛然的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