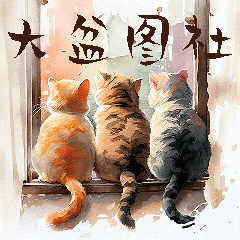《光驯服笔触之夜》
你的眉梢藏着半道虹,
而睫毛压住,
在镣铐里歌唱的碎浪。
我知晓所有关于光谱的暴政,
知悉鸢尾用假死,
篡改颜料罐的遗嘱。
当阳光给远山套上丝绒马具,
你正搅动调色碟的骨灰。
既然黄昏已晾晒,
露台是尚未受洗的钟,
既然月光探入圣餐杯时,
有人看守画室铁门。
且让苜蓿在瓷瓶里起义,
让紫藤啃食窗框的鎏金,
让所有未命名,
我们冒充早夭的春天,
练习逆光的叛逃术。
光从紫涨成橙红,
从锁孔涨成拱廊,
涨成帆索对季风的追认。
我们往松节油投递,
却收到雨季前的哑然的画框:
如何缴械焰火,
怎样囚禁流淌的钨丝,
为何锈住的窗台,
总在否认自己曾是矿脉。
未完成暴动,
悬在剃刀边缘抽芽。
绷紧的画布吞下雷云,
磨钝的琴弓,
正翻译逆风的耳语。
但总有未缴纳的绽开,
在笔触外,
构成第二片暗空:
被缴械的虹,
正游向更深的蓝。
既然每场盛开都是,
断头台边的即兴演出,
既然金箔会叛逃成陨石,
铁质会归还矿脉。
别追问维纳斯的,
像晾晒羽衣的租界那样,
我们蘸取浪沫的磷光,
却把锚,
抛进柏油中的晴空。
那些不肯着色的苞蕾在说什么?
说笔触裹着雪的胚胎,
说大理石的腹地囚着火,
说我们都在,
把未竟缝进雨衣衬里。
颜料管在战时挤出暗号:
当所有的红开始溃退,
请依然贩卖,
赭石里的晚霞黑市。
而我将继续清点:
四分音符的菌丝,
被蝉翼否决的钴蓝,
灰烬里怀孕的碑文。
失语的画刀横在,
画布与花期之间,
像大革命前夕,
被反复擦拭的燧发枪管。
可印象是游隼,
总在破晓前撕毁光谱条约。
为何斑鸠突然噤声?
为何石膏像的血管里,
突然奔涌起,
亚麻籽油未竟的咆哮?
于是我们学会用暗部驯服光,
在世纪交接的河湾,
用退潮的铰链,
放生所有溺毙的虹。
看:这不是画框,
是裹着天鹅绒的断头台。
而当法兰西在调色刀上踮脚时,
整个十九世纪正,
骑着小步舞曲的韵律,
踏碎玻璃宫殿。
可是春天啊,
你为何总在,
普鲁士蓝的暗房里显影?
为何生锈的暗房不断渗出,
湿漉漉的?
光绪年间的花香……